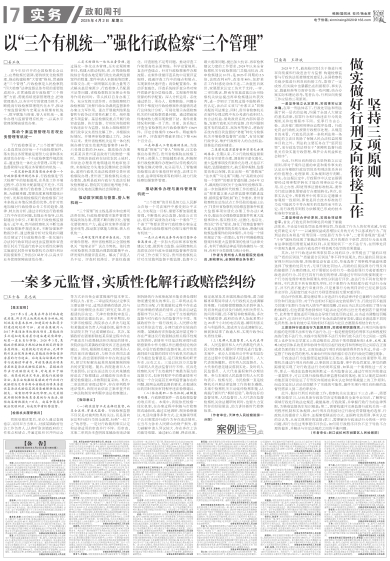2023年7月,最高检印发《关于推进行刑双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构建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制度的意见》,全国检察机关稳步推进行刑双向衔接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实践中也暴露出在衔接程序、事实认定、裁量标准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办案实际和理论思考,笔者认为,行刑反向衔接工作应坚持三项原则。
一是坚持独立认定原则,实现事实认定准确。在单一刑法体系下,行政处罚法和刑法属于同一层次的法规,均属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犯罪行为和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理机关和处理程序不同,犯罪行为由公、检、法各部门按照刑事诉讼程序处理,行政处罚由行政机关按照行政程序处理。从规范目的来看,行政处罚法第一条和刑法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目的除了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根本目的之外,刑法的主要任务在于“惩罚犯罪”,而行政处罚法则在于“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为此,行刑反向衔接应当坚持独立认定原则,即对于案件证据的审查和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根据行政处罚体系和刑法体系各自的价值理念、处理原则、实体规则进行判断。首先,在证据认定中,行政程序中认定证据需要经过刑事程序转化才能在刑事诉讼中运用,反之亦然,即使刑事证据标准较高,要作为行政证据也需要进行合理地转化;其次,在事实认定中,刑事程序中的事实认定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即使是符合技术标准的行为也可能因为不符合现实的危险性而不作认定,而行政程序则较为依赖现已形成的技术标准和专家意见。
二是坚持综合评价原则,实现处罚结果公平。首先,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均属于制裁法体系。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均造成了行为人的权利克减,行政处罚被定义为“……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而刑法的任务则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二者所体现的“惩戒”“斗争”属性均体现了制裁法的特性,其目的都在于惩罚,即其行为违反现有法律制度而需要克减其权利,从而预防其下一次不法行为,在刑事处罚中表现为量刑,而在行政处罚中则表现为处罚的效果裁量。
其次,对于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之间的区分,学界提出了“量的区别说”“质的区别说”“质量混合区别说”等不同学说观点,若以量的区别说来审视行刑反向衔接,则衔接是没有意义的,毕竟选择了刑事程序就意味着选择了较重的处罚方式,无须行政处罚加入,而质的区别说则为行刑反向衔接提供了合理的理由,对于需要区分的行为一般是轻罪行为或者重度行政违法的行为,其往往具有行政犯的特质,即通过行刑反向衔接制度对一个行为的伦理非难性和管理失序性分别进行评价,违法行为不具有伦理非难性,不代表其不具有管理失序性。对于重罪行为和轻度行政不法行为而言,并不代表不能进行双重评价,只是重罪行为的刑罚评价已经足够包容其余评价,而轻度行政不法行为则显然较轻无需双重评价。
综合评价原则,即处理结果上对违法行为的法律评价应兼顾行为的刑法评价和行政法评价。对于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轻罪行为,行政处罚不能因为其属于犯罪行为而列入情节严重的范畴,反而应当以其已经承担了罪行而酌情减轻,但也需要考虑到相对不起诉决定的作出往往考虑到若干量刑情节,此类情节重复适用可能也会导致行政处罚的过轻,应当适当调整处罚幅度。此外,应当针对不法行为对于社会法益的侵害类型,建议妥善选取不同的处罚类型,如有的地方采用的相对不起诉与社区志愿服务相结合的方式。
三是坚持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原则,实现检察职能做实。行刑反向衔接所衔接的是刑事不法和行政不法行为,且一般是程度较轻的刑事不法和程度较高的行政不法行为,实践中发现刑事不法行为和行政不法行为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生态学意义上的边缘效应,即由于某些裁量标准(主体、主观、客观)或处罚体系的差异和协同作用而引起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之间存在正面或者负面的较大变化,正面如通过行刑反向衔接使得其罚当其过,并进一步监督了行政处罚的使用,反面如行刑反向衔接中存在的行政处罚倒挂现象。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便是起到强化正效应,弱化负效应的重要作用,检察机关通过行刑反向衔接,以事前的立案监督、事中的处罚意见、事后的跟踪督促实现了对行政违法行为的闭环监督。如果说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那么一项违法监督机制则胜过一系列监督会议,通过行刑反向衔接这一重要抓手,可以实现行政检察法律监督权威的落地。前文从规范层面和功能层面分别论证了行刑反向衔接在事实认定和结果裁量上的工作原则,而这仅是在认识论层面赋予了实践的可能性,最终实现行刑反向衔接的监督仍需深入到二者的职权中。
此外,做好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检察机关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需要不断加强学习,从而具备行政处罚决定和裁量的全套专业知识,了解特定领域行政处罚的法定规范、裁量基准、行政政策,并掌握行政行为的法律界限,为精准监督筑牢知识根基;第二,需要构建并完善监督行政机关的一系列程序机制和实体规则,如行刑反向衔接对应行政处罚管辖地的选择、行政机关的提前介入程序、证据案卷移送的方式、证据转化的原则、事实认定的互认等,从而实现更好的监督;第三,需要解决行政违法行为的统一评价问题,即行为经过刑事程序评价后,如何用行政程序评价不至于导致不合理的偏差,并解决与实定法规范之间的平衡问题。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